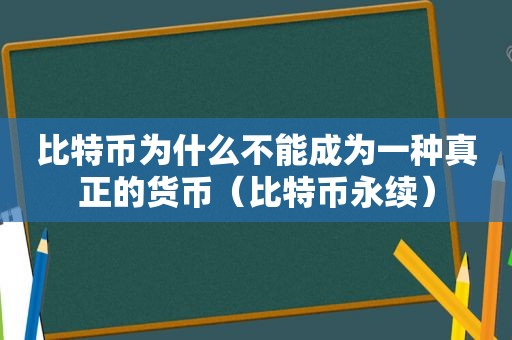本
文
摘
要

本故事比较长,接下来更精彩————第二天各份报都竞相登载了“布瑞克斯顿奇案”——他们是这么称呼这个案子的。每份报纸都做了长篇累牍的详细报道,有的还同时发表了评论。其中提到的情况,有些是我原先不知道的。我的剪贴本里至今还留着许多这件案子的相关剪报和摘录。下面是经过整理的一部分:《每日电讯报》评论道,迄今在犯罪史上情节如此离奇的案件还是很少见的。遇害者用的是德国名字,凶手全无其他作案动机,加上墙上
留下的恐怖血字,都说明作案的是政治难民和革命党人。在美国社会
党有许多支部,死者无疑触犯了他们的某项不成文法规,因此被一直跟
踪到了英国。文章还旁征博引,谈及了秘密刑事法庭制度,托法娜毒药
水,意大利烧炭党人,德·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以至雷克利弗公路谋杀案,得出的结论是要告诫 *** 当局,加强对于在英国的外国人的防范。
《旗帜报》则指出,这类无视法律权威的暴行,通常会发生于自由党的执政期间。这源于民众心智上的不健全,以及由此引起的种种职权的软弱。受害者是一位美国绅士,在伦敦已经逗留几个星期。他住在坎伯韦尔区托凯街夏庞蒂埃夫人的公寓。他由他的私人秘书约瑟夫·斯坦节逊先生陪同来到伦敦。两人于本月四日星期二告别了房东太太,便到达尤斯顿车站,打算乘快车前往利物浦。有人在站台上看到过他们,而此后就再也没人见过他俩了,直至发现了德雷伯先生的尸体,有如报道所载,被放在距尤斯顿数英里之遥的布瑞克斯顿街的一幢空宅里。他怎样到了那里,又怎样在那儿惨遭伤害,至今仍是未解之谜。斯坦节逊至今下落不明。所幸,我们获悉由苏格兰场的雷斯垂德先生和葛莱森先生联合负责办理此案,相信这两位能干的警探定能迅速破案。
《每日新闻》认为此案肯定是一桩政治案件。大陆各国的 *** 都积极推行专制政体,对自由党的主张则极为排斥,后果就是驱逐了一大批因有前科而颇难成为好公民的人离开英国境内。这些人中有一套极其严格的规范,一旦触犯,则处以死刑。眼下应尽最大努力找到死者的秘书斯坦节逊,以查明死者生前的爱好习惯和种种细节。死者之前住过的公寓地址已查明,这使案情有了很大的进展,这完全要归功于苏格兰场葛莱森先生的机警和精干。
福尔摩斯和我在早餐时一起阅读了这些文章,这似乎让他感到十分有趣。“我跟您说过吧!不管情况如何,雷斯垂德和葛莱森都是赢家。”
“那也得看看案子的结果吧。”
“哼,根本没有任何关系。要是逮住了这家伙,那就是他们尽心职守,终于成功;要是他跑掉了,那他们也已经尽了全力,只是运气不佳。反正他们总是有道理的。无论他们做什么,总有人出来捧场。‘一个蠢货再蠢,也会有个更蠢的家伙崇拜他。’”
“这人是怎么回事?”这时我不由叫了出来,因为我听到门厅和楼梯上传来嘈杂的脚步声,其中还夹杂了房东太太的埋怨。“侦缉队的贝克街小分队来了。”我的朋友一脸正经地说。
话音还没落下,只见6个街上的流浪儿冲了进来,身上脏成这样衣服破这样的小混混儿,我还真是头一次见呢。
“立正!”福尔摩斯严厉地喝道,这6个小混混立刻站成一排,像极了几尊破破烂烂的泥塑。“以后只能由威金斯一个人进来向我报告,剩下的人都得等在街上。那么你们找到他了吗,威金斯?”
“没有,先生,我们还没有找到。”其中一个孩子回答。
“我倒也没指望你们这么快就找到,但你们必须继续找,一直到找到才行。这是你们的工资。”他给他们每人发了一个先令。“好啦,你们走吧!下回要带些好消息过来。”他挥了挥手,这群孩子就像耗子似的一下子蹿下楼去,不一会儿街上就传来了他们的尖叫声。
“一个这种小混混,比一打警察还有用。”我的同伴说,“人们只要一看到像警察一样的人,就闭上嘴不说话了。可这些孩子,哪儿都去得了,什么都打听得到,而且他们每一个都是机灵鬼,唯一缺的就是组织性。”
“您雇用了他们帮您查这桩案子吗?”“是的,有件事我要确认一下,这只是时间问题。哈!我们马上就要听到好消息听了!葛莱森一路往这儿走来,一脸的春风得意。我知道,他一准儿是来找我们。看,他站住了。到门口了。”
果然楼下马上就 *** 大作,几秒钟后,那位金发的侦探疾步地奔跑着上楼来,闯进了楼上的房间。“老兄,”他握紧着福尔摩斯回应冷漠的手喊道,“祝贺我吧!整个案情已经被我侦破得水落石出了。”
我似乎看到我这位同伴表情丰富的脸上闪过了一丝不安的神情。
“您是说,您找到了可靠的线索?”他问。
“可靠的线索!这话说的,朋友,我们已经把那家伙关在牢里了。”“他的名字是什么?”
“阿瑟·夏庞蒂埃,皇家海军中尉。”葛莱森万分得意地搓着他肥胖的双手,挺着胸脯大声说。
歇洛克·福尔摩斯呼了一口气,轻松地微笑了。“请坐,来抽根雪茄吧。”他说,“我们万分急切地想知道您怎么破的案。要不要再来点威士忌加水?”
“不妨来一点吧!”这位侦探回答说,“这几天我尽心竭力,简直是弄得筋疲力尽。您知道,尽管体力上并没有太大的消耗,可是心理上却要承受很大的压力。您对此一定是深有体会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可是从事脑力劳动的同行啊!”
“您这么说我实在是不敢当。”我的同伴一本正经地说,“给我们讲讲您是怎么获得这个令人高兴的成功的。”
这位大侦探在扶手椅上坐定,扬扬得意地吸了口雪茄,而后就乐不可支地突然在大腿上猛拍一下。“妙就妙在,”他大声说,“那个蠢货雷斯垂德自以为是,可是根本就走了条岔道。他一心想要揪住那个秘书斯坦节逊,可那人在这桩案子里清白得就像初生的婴儿一样。我敢肯定,他现在已经把那可怜的人给逮捕了。”
葛莱森说到这儿,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一直笑到上不来气。“那您是如何找到线索的呢?”“硬、让我来从头开始告诉你们吧!当然,华生医生,这事可绝不能让其他人知道。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弄清这个美国人的来历。换了别人,也许会一直傻等登报的启事的回音,也许情人会主动来提供什么信息。这些可绝不是托比亚斯·葛莱森的作风。你们还记得尸体身边的帽子吗?”
“记得,”福尔摩斯说,“那是在恩德乌德父子的店里买的,在坎伯韦尔街129号。”
葛莱森看上去蛮沮丧。
“我没想到这您也发现了。”他说,“您去过那儿吗?”
“没有。”
“哈!”葛莱森喊道,像是松了口气一样,“一个人不应该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即使看上去它是那么微不足道。”
“对有出众智慧的人来说,不存在什么微不足道的事情。”福尔摩斯简明地回答。“好,我去了恩德乌德的店里,向店主询问有没有卖过这种尺码和式样的帽子。他翻看了销售记录,很快便找到了。这顶帽子是送去给德雷伯先生的,他住在托凯街夏庞蒂埃寄膳公寓。由此我就弄到了他的住址。”
“漂亮……太漂亮了!”歇洛克·福尔摩斯轻声地说。
“我马上就去拜访了夏庞蒂埃太太。”侦探继续说下去,“我看到她脸色发白,神情忧虑。她女儿也在房里——那姑娘长得很美;看上去她眼圈红红的,讲话时嘴唇还一直在打哆嗦。这当然逃不过我的眼睛。我寻思着这下有戏了。这种感觉到自己的侦缉对了路的情况,福尔摩斯先生,您肯定能了解的——浑身的神经似乎都绷紧了。‘你们以前的房客,克利夫兰的伊诺克·J.德雷伯先生被人伤害的消息,你们知道了吗?’我问。”
“那位母亲点了点头。她看上去都说不出来话了。她女儿却一下子哭了出来。这下子我更确定了这两个女人一准儿是对这桩案子知情的。”“德雷伯先生是几点钟向你们告辞去火车站的?’我问。”“八点钟。’她说,喉头哽着压抑内心的感情,‘他的秘书斯坦节逊先生告诉她有两趟火车,一趟是九点十五分开,一趟是十一点开。他准备坐前面一趟离开。’”“这就是你俩跟他的最后一次见面吗?”
“这话刚一出口,那个女人突然变了脸色,完全变成铁青色了。好一会儿之后,她好不容易才说出了‘是的’两个字……而且声音沙哑,语调极不自然。”
“经过了一阵沉默,她女儿以平静、肯定的声音开口了:‘说谎不会有任何好处的,妈妈。我们还是告诉这位先生实情吧。我们后来确实又跟德雷伯先生见过面。’”
“‘愿上帝宽恕你!’夏庞蒂埃太太双手高举,瘫坐在扶手椅里,‘你这是害了你哥哥呀。’”
“‘阿瑟也会希望我们讲出实情的。’姑娘坚定地回答。”
“‘您现在最好把事情毫不隐瞒地告诉我,’我说,‘只讲一半的话、那倒不如不说。况且,您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已经掌握了什么。’”…这都要怪你,艾丽丝!’母亲喊道,然后,她转向我说:‘我会告诉您一切的,先生。请不要认为我为儿子感到如此不安,原因是怕他与这
桩可怕的案子有任何牵连。他在这件事情上完全是清白的。我怕的只是在您或别人的眼里,他似乎脱不了干系。但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凭
他高尚的人品、职业、经历,他都是绝对不会做出那种事情的。’”
“‘您最好的选择就是把事情一一讲明。’我说,‘请您相信我,您儿子如果真的是无辜的,我们是决不会冤枉他的。’”
“‘艾丽丝,或许最好让我单独跟这位先生谈谈吧。’她这么说了之后,她女儿就出去了。”
“‘好吧,先生,’她接着说,‘我原来是没准备把这一切都说出来的,
可是既然我可怜的女儿已经将事情讲了出来,我也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一旦决定了告诉您,我就会把事情毫无保留地全都说出来。’”
“‘这是最明智的做法了。’我说。”“德雷伯先生住在我们这儿差不多有三个星期。他和秘书斯坦节逊先生来欧洲旅行。我看见他们的箱子上都贴了哥本哈根的旅行标签,知道他们刚打那儿到伦敦。斯坦节逊是个矜持、沉静的人,而他的东家,说实在的、跟他截然不同。这人生性放荡,言行粗俗。第一天晚上他就喝了个大醉,直到第二天中午以后都还没有完全清醒。对女仆的态度更是随便得放肆。而更糟的,是他很快就对艾丽丝也露出了这副德行,多次对她说一些不堪入耳的混账话,多亏单纯的艾丽丝还听不懂这些。有一次,他居然抓住了她的手,抱住了她……他这样胡作非为,甚至连他自己的秘书都指责他。”
那您为什么容他这样做呢?’我问。‘我想,只要您愿意的话,您尽可以让您的房客离开。’”
“我问到了要害之处,夏庞蒂埃太太不由得红了脸。‘如果在他来的当天我就回绝了他,那就好了。’她说,‘但这真是个有些难堪的诱惑。
他们每人每天向我支付一英镑——一星期就是十四英镑,并且这本来
就是租房的淡季。我是个寡妇,儿子在海军服役又需要花很多钱,我不愿失去这笔收入,所以我就只能尽量忍受。可他最后那次实在是太过分
了,所以我马上让他搬走了。这正是他离开的原因。”“后来呢?”
“看到他乘的车子走了,我暗暗地松了口气。那时我儿子正好在家休假,但这事儿我却对他只字未提,因为他性子暴躁,又很疼妹妹。他们走后,我就关上房门,真是感到心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唉,可是谁想到还没过一个钟头,门铃响了,那位先生又回来了。他异常兴奋,显然是又喝醉了。我的女儿当时正坐在房里,他便闯了进来,语无伦次地解释着什么火车误了点。接着他转向艾丽丝,竟当着我的面请她跟他私奔。‘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说,‘没有任何法律可以阻拦。我可有的是钱,完全够你花的。甭管这个老太婆了,跟我一块儿走吧。你的日子会过得像个公主一样。’可怜的艾丽丝被吓得一直后退,可是他紧抓着她的手腕,一直把她往门口拖。”
“我尖叫起来,就在这时,我的儿子阿瑟进了屋。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当时只能听见乱哄哄的咒骂声和扭打的声音,我吓得没敢抬头看。当我抬起头时,只见阿瑟站在门口大笑着,手里有一根棍子。‘料想这小子再也不敢来找咱们麻烦了,’他说,‘我出去看看他还想怎么样。’然后,他就拿起帽子下了楼。第二天早上,我们便听了德雷伯先生遭到毒手的消息。”
“这都是夏庞蒂埃太太亲口告诉我的,不过她当时说得断断续续的,不时还要停下来喘气儿,有时候她的声音低得让我差点儿就听不清,不过,她的每一句话,我都速记了下来,所以绝没有弄错。”
“十分精彩。”歇洛克·福尔摩斯说着,一边打了个哈欠。“那后来呢?”
“听完夏庞蒂埃太太的话以后,”这位侦探接着说,“我发现整件案子的关键所在了。我用眼睛紧紧盯住她,我发现这种眼光在女人身上往往十分奏效,然后我问她,她儿子是几点钟回家来的。”
“‘我不知道。’她回答说。”“不知道?”
“是的,他有家里的钥匙,我们用不着等他。”“那么,他是在您睡觉之后才回来的?”“是的。”
“您是几点钟休息的?”“大约十一点。”
“这么说,您儿子出去了至少有两个钟头?”“是的。”
“也许是四五个钟头?”“是的。”
“他在出门的这段时间里都做了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她说这些时,嘴唇已经全无血色。”
“话说到这儿,也就没什么好再问的了。我设法打听到了夏庞蒂中尉的下落,带了两个警探去逮捕他。就在我抓住他的肩膀,警告他实地跟我们走的时候,他却突然放肆地问我:‘你们逮捕我,想必是怀我跟那个 *** 德雷伯的死有关吧?’这件事我们还没向他提过呢,他己倒先问了,这就相当可疑了。”“的确如此。”福尔摩斯说道。“他身旁还有那根沉甸甸的木棍,他母亲说他就是拿着这根木棍去追打德雷伯的。那是根很粗的橡木棒。”“那么,您得出了什么结论呢?”
“哦、我的结论是:他在德雷伯后面,一直追到了布瑞克斯顿街。在那里,两人又发生了争吵,在此过程中德雷伯被他打了一棒,这一棒很可能是击中了他的腹部,所以虽然致命,却没留下任何痕迹。那天晚上下了很大的雨,四周没有其他行人,所以夏庞蒂埃就把德雷伯的尸体拖到那座空宅里。至于什么蜡烛啊,血迹啊,写在墙上的血字啊,还有戒指,其实都是他故意布下的迷阵,是想要把警方的侦查工作导向歧途。”“说得好!”福尔摩斯称赞道,“真的,葛莱森,您进展太大了。成功
就在眼前了。”
“我要说的是,这件事我处理得相当利索。”这位侦探沾沾自喜地回答,“那个中尉自愿写了一份陈述,说在跟踪了德雷伯一会儿之后,被德雷伯发现了,受害人就乘上一辆马车把他给甩掉了。在回家的路上,他遇见一个在军舰上的同事,两人一起走了一段很长的路。可问到他那个同事在哪儿住时,他又没法圆谎了。我觉得整件案子的每一个细节现在都可以吻合了。让我觉得好笑的是想到了雷斯垂德,他从一开始就错了方向。我怕他不见得会有什么收获喽。哟,他倒也来了!”
来者确是雷斯垂德,他上楼梯时我们还在谈话,此刻他已走了进来。他平时在言谈和着装上表现出来的自信与风度,这会儿全没了。
他神色慌张,六神不定,而且衣冠不整,乱七八糟的。想必他是来向歇洛克·福尔摩斯求教的,可一见同事也在场,顿时又很尴尬,有些手足无措。他立在房间中央,神经似的摆弄着手中的帽子,不知该做什么好。
“这桩案子真是玄妙离奇,”最后他终于开口了,“实在是叫人难以理解!”
“哈,您是这么想的吗,雷斯垂德先生!”葛莱森得意地喊道,“我也料到您会有这么个结论的。您设法去找那个秘书约瑟夫·斯坦节逊先生了吗?”
“那个秘书约瑟夫·斯坦节逊先生,”雷斯垂德面色严肃地说、“今晨六点钟左右在哈利迪内部旅馆被人谋害了。”——……未完待续。节选白福尔摩斯探案集。